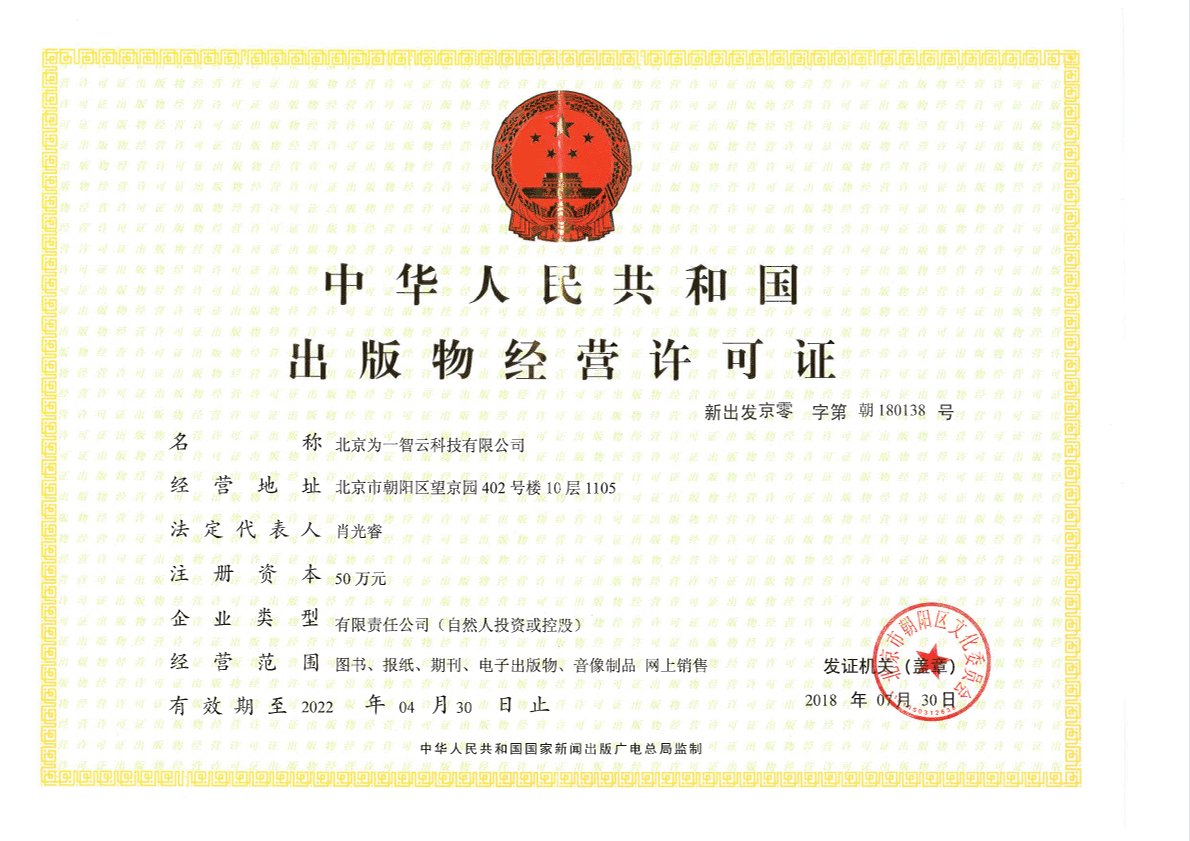作者簡介:方榕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在中國不是新鮮事物,但是自2014年大面積推廣以來,引發了諸多關于基本問題的爭論,也遭遇了一系列中國市場特有的實踐困惑。相信《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PPP條例”)的制訂將有利于澄清困惑、凝聚共識,推動PPP的發展再上新臺階。但是從發揮法律引領實踐的作用而言,PPP條例征求意見稿還有可改善空間。
立法的目的之一在于回應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但不應僅著眼于解決現有的問題,或者被實踐問題“綁架”而淡化高位階的頂層制度設計。征求意見稿體現的立法目的是“規范”,但立法應有一定前瞻性,發揮引導作用,建議將“促進”同時列為立法目的。一方面,規范的目的是為了PPP模式的良性發展,達到新的發展階段和層次,是為促進;另一方面,PPP是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和提升公共服務效率的有效路徑之一,應當繼續推行并鼓勵發展。
在PPP于中國市場混沌初開百家爭鳴的局面下,PPP條例應有所為有所不為,聚焦于厘清基礎法律關系、基本概念和基本問題,確立物有所值評價、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等核心制度和理念,對于操作性較強,特別是尚未經過實踐檢驗的操作范式、實施流程等,不建議在立法層面固化操作,以避免倉促立法又不斷“打補丁”式修法。
作為PPP條例確立的基本制度的補充,應充分發揮配套政策、操作指引和示范合同的作用,在微觀層面允許試錯和創新,通過實踐迭代形成適于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模式的操作規程,且無需整齊劃一。
無論是英文的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還是中文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其核心都是“合作”,民事法律關系屬性是合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即便涉及政府授權的特許經營,政府的行政監管也是以合作為前提。
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律性質的界定有較多爭論,加重了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參與PPP的顧慮。征求意見稿雖然肯定PPP的原則之一是“平等協商”,認可通過仲裁途徑解決PPP相關的爭議,但是對于何為民事屬性的爭議何為行政屬性的爭議未做區分,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不強,建議肯定PPP的民事法律關系屬性,對適用民事爭議解決的事項予以適當明確。
特許經營和政府采購均是PPP的大類之一,但是二者在法律關系、回報機制、合同條款體系等重要方面均有區別,政府在不同類別項目中的角色和定位也略有不同。將特許經營和政府采購同納于PPP條例之下有利于不同類別PPP項目的統一操作,澄清當下實踐中的一些困惑。但是,采用同一條款籠統規制兩類不同的項目難免會有技術困難,一定程度上導致征求意見稿的條款適用針對性不強,或者邊界模糊。建議對特許經營項目和政府采購項目在發起和實施環節分列專章進行規范,或者以專章規定特許經營項目相關的授權、壟斷行業管制、普遍服務、價格調整等事項,加強法律條款的可操作性。
征求意見稿全文大量使用“有關部門”,雖能理解立法者的不得已,但無助于回應市場對神仙打架的困惑。
PPP項目較多涉及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改革部門作為綜合經濟管理部門,傳統上主管宏觀調控和固定資產投資,由其從立項審批、投資控制、價格管制等角度統籌對PPP項目的管理,有利于在現有部門分工格局下加強對PPP項目的協調。財政部門負責政府收支管理,在PPP領域側重于涉及政府支付事項的審查、決策和監督,從政府支付義務管理角度嚴控PPP模式下政府不合規舉債,督導物有所值評價制度的執行。
較之2002年由建設部主導的公用事業行業市場化改革,本輪PPP的推廣中行業主管部門相對缺位,發揮行業主管部門在項目發起、績效評價、日常監管等方面的作用,可以在不同行業個性化地發展PPP,充分發揮PPP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方面的效率優勢。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下,建議PPP條例明確政府部門之間的分工,在項目實施層面賦予地方行業主管部門更多的職能和職責,提高PPP項目微觀層面的管理水平。
“泛化”成了PPP圈的熱詞,蓋因確有不少不適于采用PPP的項目以PPP的方式運作。在PPP運用成熟的國家,PPP只是傳統政府投資的一種補充,且需要通過嚴謹、周密的前期工作確定具體的項目運作方式和交易條件。運動式PPP恰與以上兩點背離,一是不分行業、不分項目、無論市場是否成熟、項目邊界條件是否清晰,一概PPP,甚至為了PPP而PPP;二是前期工作草率,即便有前期工作,流程意義也遠大于項目財務經濟測算、科學分配項目風險、細化績效考核機制方面的意義。
市場不應只討論PPP項目“落地難”,先天不足的項目本來就不應該做PPP。PPP條例有能力也有必要從立法層面對此予以必要引導,明確物有所值評價要求、強調實施方案的編制應以完成可研立項和財務測算為前提,強調PPP項目應當明確運營績效監管要求等等,以提高PPP項目的適用門檻,提升項目質量,從而根本性地解決PPP項目融資難等問題。
物有所值是PPP項目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PPP項目篩選的重要原則和方法。要求PPP項目通過物有所值論證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PPP項目的泛化,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雖然物有所值評價在我國現有市場環境下未得到充分落實,實踐中也存在流于形式的問題,但這不是物有所值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健全物有所值評價體系的問題。引入物有所值評價是規范PPP的目標和發展方向,應作為一項基本制度予以固化,將物有所值評價作為開展PPP的規定動作,并配套完善物有所值評價標準和技術細則,引導和規范物有所值程序真正發揮作用。
征求意見稿使用的“必要性、合理性評估”與物有所值的內涵相差甚遠,且實際操作中彈性空間更大。即便不采用物有所值的提法,也應對“必要性、合理性”的外延及評價方法予以明確界定和制定細則,起到評估項目采用PPP模式是否確實優于傳統政府投資,以及具體采用何等PPP模式的作用。
征求意見稿對PPP項目的融資問題著墨甚少。一方面,融資難是當下PPP實踐的痛點之一,不培育和健全針對PPP項目的融資市場,PPP的發展將失去動力引擎;另一方面,雖然大量金融機構參與了這一輪的PPP,但普遍更關注地方政府、社會資本方的主體信用,鮮見關注項目情況并運用項目融資邏輯的融資案例。
成熟的PPP市場鼓勵項目融資,通過有限追索或無追索融資安排倒逼PPP項目的穩健財務測算和項目風險分配。中國的金融市場還沒有發達到可以真正實現風險報酬定價,對PPP項目的融資也過于倚重主體信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PPP市場的亂象。立法應當促進和鼓勵基于項目信用的項目融資,引導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理性參與PPP項目。建議PPP條例明確“鼓勵金融機構通過有限追索方式為PPP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發揮金融資源配置對市場的反向調節作用;同時,引導金融機構樹立項目融資理念,逐步建立對PPP項目的風險報酬定價。作為與此配套的具體措施,PPP條例應將設立項目公司開展PPP項目作為制度常態,應當鼓勵在實施方案編制階段公開征集金融機構對實施方案的意見,且條例應為項目融資的配套機制,如提前終止情況下的補償應視情況全部或部分覆蓋未償金融債權本息、金融機構可以擁有介入權等,留下空間和接口。
[i] 本文節選和改編自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就PPP條例征求意見稿向國務院法制辦反饋的意見和建議,李小、王雪音、沈雨竹、田琦、劉京、聶曉迪、李強等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