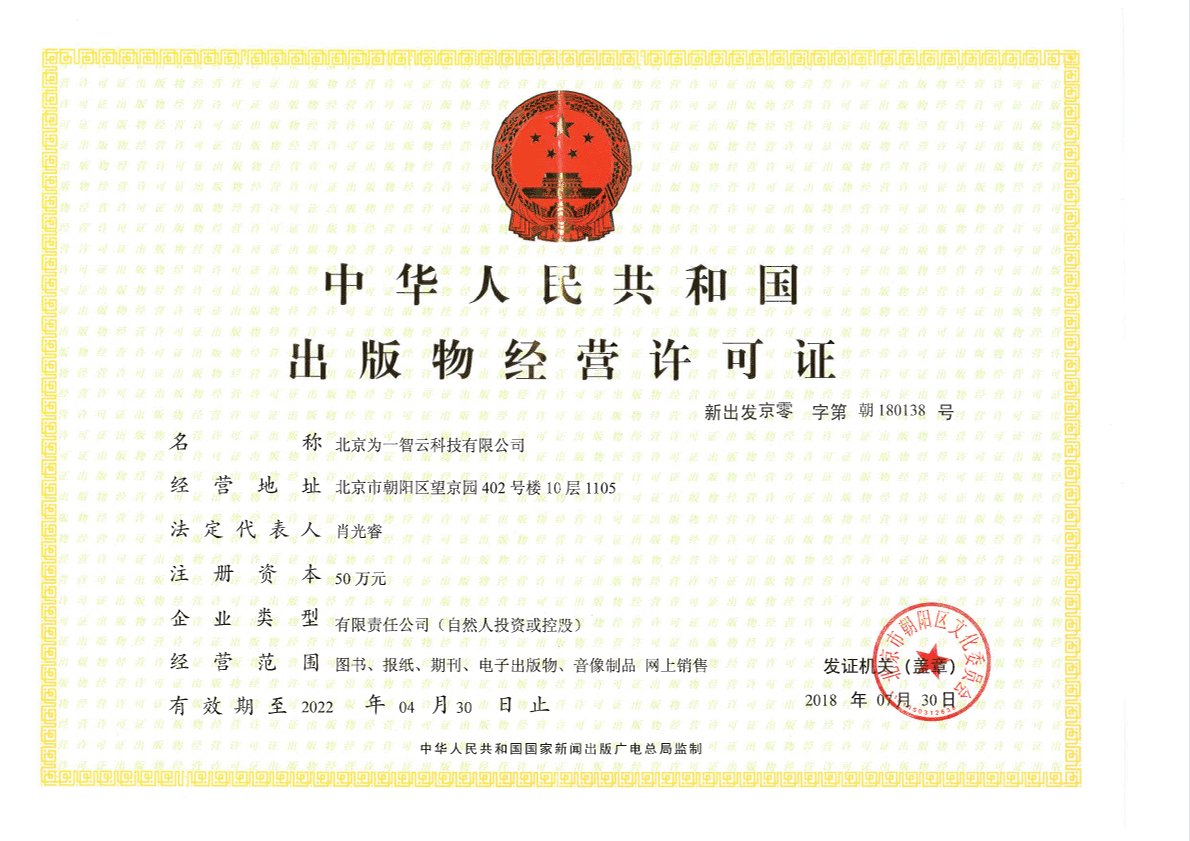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大信號。
本周三晚,國務院印發了一份《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直指央地關系。
央地財政關系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會深刻塑造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改變此后數十年的投資行為。
四十年前,財政大包干結束了“大鍋飯”體制,“分灶吃飯”給地方下放了更多的自主權,社會積極性極大釋放,諸侯經濟崛起。
二十多年前,分稅制改革挽救了一場中央財政危機,財政收入開始向中央快速高度集中,“鐵公基”的序幕也從這里拉開。
今日,央地關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這會是繼分稅制時隔二十年的又一次顛覆式變革嗎?
01
這次改革,是增加地方自主權的信號之一。
改革方案的內容有三條:
一是保持增值稅“五五分享”比例穩定。
二是調整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
三是后移消費稅征收環節并穩步下劃地方,將部分在生產(進口)環節征收的現行消費稅品目逐步后移至批發或零售環節征收。
簡單說:
1. 消費稅以后要全部交給地方了。
此舉直接給地方增收。2018年國內消費稅有10632億元,現在中央稅轉移給了地方,是財權的下放。
短期來看,最直接的利好是——地方有錢之后,又有動力加大基建投資,符合穩增長的目標。
但從長期來看,地方政府必然要調整思路,想盡辦法促進終端消費,營造更好的消費環境,比如旅游開發、餐飲服務、夜間經濟等,這和“擴大內需”的施政邏輯是一致的。這個在后面我會再解釋。
2. 稅收最大頭增值稅分成定下了,從以前的央地75%/25%分,變成央地五五分。
央地在增值稅的分配比例原本是75%/25%,2016年營改增后,地方政府的營業稅收入直接被砍掉,為了彌補缺口,當時是通過增值稅五五分的方式暫時過渡。此次增值稅改革仍保持五五分,給地方政府吃下了一顆定心丸,蛋糕沒有少。
另外,調整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也是給地方減負。
02
歷來中國央地關系的重大調整,背后無不伴隨著一場場的博弈和較量。
在改革開放后,中國一直實行財政包干制,各省和中央簽承包合同,定好交多少稅,財政收入多了也不會多交。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地方口袋里的錢多了,而中央卻越來越“窮”,對財政大局的控制力日漸削弱。
從1988年開始,財政部連續三年需要向地方政府借錢,到了1991年時,劉仲藜對朱镕基說,他切身體會到舊小說中常說的“國庫空虛”了。
這才有了1994年那場分稅制改革,重新將稅源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央地共享稅,將地方上的稅收更多地提到中央來。
1993年9月到11月這兩個月的時間里,朱镕基帶著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一個個地做工作。
讓最大的受益者割讓蛋糕,難度可想而知。廣東的財政包干體制運行力度大,對分稅制也明確表示了抵觸態度,這里也是最關鍵的一場硬仗。
時任財政部長劉仲藜的回憶稱,廣東兩位主要負責人找到朱镕基,談了兩個多小時。他們問朱镕基,廣東的特殊政策還要不要實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們還要不要在20年內趕上 “四小龍”?按財政會議上所提出的辦法,廣東就什么大事也不干了。廣東省給了朱镕基兩張表格,對比包干制10年不變和分稅制實行10年后的財力對比,中央要從廣東多拿走1000多個億。
如果一個分稅制把廣東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龍”,問題可就大了。朱镕基當夜就把財政部長和地方預算司長叫到房間,連夜重新測算,最后少拿了300億,但蛋糕做大了,地方財政也有了更大增長。
在一波三折的討價還價中,廣東最終還是顧全大局,同意實行分稅制。事后朱镕基半開玩笑地說,那段日子是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實行分稅制,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商量,妥協,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5斤肉。”
二十年前的分稅制改革是救中央財政危機,那么這場新時代的財稅改革又是為了救誰?
03
答案不言而明,這次是要“救”地方。
此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很明確,“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支持地方政府落實減稅降費政策、緩解財政運行困難”。
近兩年來,前所未有的房地產調控使得有些地方土地流拍,影響了土地財政收入,而打擊影子銀行又讓40萬億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加。
這些后果,可以說是分稅制二十年來的后遺癥。
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從75%驟降到53%,而地方財政支出占全國的比例卻從70%躥升到85%。在公共財政支出的最大頭“教育”中,地方負擔達到90%以上。


財權上收,事權卻下沉,這種長期扭曲的財政行為削弱了地方的財政自給能力,導致基層政府在稅收無法滿足的情況下,只能擠占其他公共支出,或者舉債度日,甚至拖欠工資。
2018年中發生的事情還歷歷在目,某省出現教師討薪,到某市出現全國首例地方政府拖欠公職人員薪資事件,再到南方某地主管領導“恐嚇”金融機構配合政府還債……今年連帝都的財政局長都公開喊窮,向上級要錢支持。
可想而知,目前地方財政有多希望甘露降臨。
去年,企業信心在所謂“國進民退”問題上一度低迷,疊加內外部經濟變化,中央開啟了一場萬億規模的減稅降費。中央想要減輕企業負擔的意志,需要地方不打折扣地執行。
如此一來,中央就得想盡辦法減輕地方的負擔,用增值稅五五分穩住地方,用消費稅下劃補貼地方。
當然,以前的稅制也有中央的考量,大部分的增值稅、以及全部消費稅全部劃歸中央,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地方保護和市場割據行為。
比如,消費稅大多是在生產、進口環節征收,大頭是油、煙、酒、汽車。如果以后征收方式不變,不排除地方為了擴大稅基而爭搶這些中央不鼓勵的企業,造成低效競爭。
該怎么辦?現行改革通過“后移征收環節”來避免上述情況的發生。
消費稅從生產、進口環節后移到批發、零售環節,以前由企業交的消費稅,現在經銷商、消費者也要來交。
換句話來說,A市如果為了更多的消費稅,引入煙酒企業、擴大生產是沒有用的,最后這筆稅可能是歸該產品的消費地B市所有。
這次只選了一些征管條件成熟的小稅目比如高檔手表、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先行改革,以后再穩步推其他品目。
昨天因為中金公司《后移消費稅征收環節將對白酒產生一定潛在影響》的報告,白酒股開盤驚魂跳水,茅臺更是直接下挫3個百分點。雖說目前改革試點不涉及白酒,但長遠來看,這些高端品類的消費稅都會慢慢征收上來的,畢竟這比房產稅的征收壓力小得多。
04
必須點明的一點是,此次改革沒有涉及央地的事權變更。
財政改革的主線很大程度上還是在于解決政府間的收入和分配問題,也就是如何在確保上級收入的同時激勵下級政府開源節流,事權方面的調整相對較慢。
不過,從本輪財稅改革的內在邏輯來看,增加地方的自主權、緩解地方財政壓力是大趨勢。
比如,對經濟舉足輕重的房地產,在調控方式上出現了“因城施策”。
比如,大都市圈時代下自貿區的接連成立,讓地方改革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
比如,3萬億的教育經費支出的分擔上出現事權新調整,央地共擔比例增加。
比如,地方債的開閘,將地方債務從隱性慢慢轉向顯性,也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財政透明度和約束性。
財政聯邦主義正在慢慢回歸。
財稅改革加速,央地關系在發生本質性變化。
美國經濟學家Arthur Kroeber說過,如果地方官員的激勵機制改革停滯不前,那么其他的改革設計得再巧妙,也有可能會失敗。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步步邁入深水區,改變地方激勵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將重心從資本密集型工業轉向消費者導向型的服務行業,將會是最大的看點。
參考資料:
《新中國經濟70年·分稅制|親歷者劉仲藜:分稅制化解中央財政危機》
《王丙乾:我國分稅制決策背景歷史回放》
《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