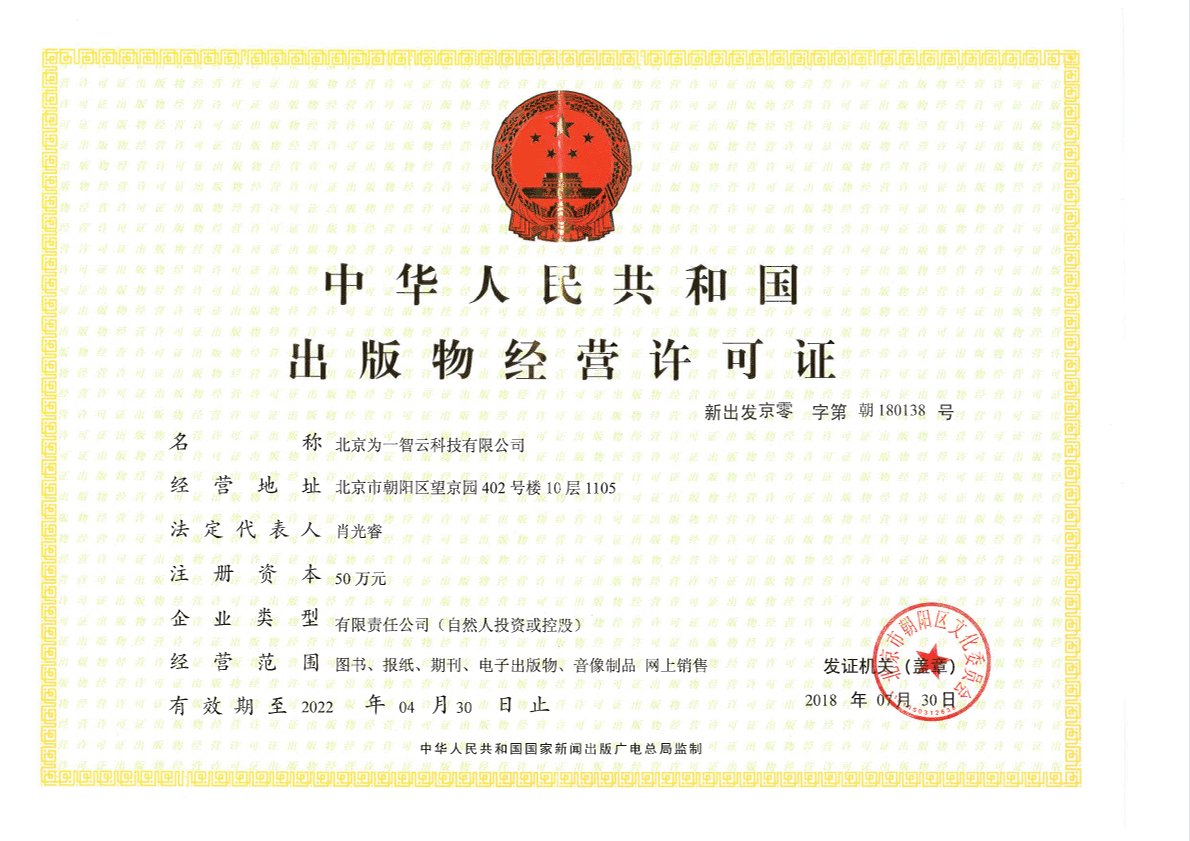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guān)于審理行政協(xié)議案件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司法解釋?zhuān)?ldquo;礦產(chǎn)等自然資源開(kāi)發(fā)”“保障房”和“PPP”這三個(gè)巨大的市場(chǎng)將被納入行政庭的管轄權(quán),這種改變勢(shì)必沖擊這三個(gè)專(zhuān)業(yè)市場(chǎng)的預(yù)期,并改變相關(guān)市場(chǎng)行為
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對(duì)政府和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和邊界提出了新命題。同時(shí),放松經(jīng)濟(jì)規(guī)制也是中國(guó)改革的核心動(dòng)力源之一。與此相應(yīng),公共產(chǎn)品、公共服務(wù)的市場(chǎng)化,都已成為中國(guó)和其他國(guó)家共同采取的方案。
中國(guó)政府正在不斷開(kāi)放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wù)市場(chǎng),從1984年的交通領(lǐng)域開(kāi)始,逐步地引入了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和自發(fā)合作模式。再后來(lái),發(fā)展到自然資源的開(kāi)采,以及近年廣泛開(kāi)展的政府和社會(huì)資本合作(PPP)。這兩個(gè)市場(chǎng)之中最近發(fā)生的法律上的大事,是其中涉及到政府一方的合同行為,剛剛被劃為“行政協(xié)議”。
2019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guān)于審理行政協(xié)議案件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的司法解釋?zhuān)ㄏ路Q(chēng)司法解釋?zhuān)瑢PP和礦業(yè)市場(chǎng),加上政府投資的保障性住房所涉的合同或協(xié)議,歸入了法院行政庭的管轄范圍,引發(fā)了業(yè)界的強(qiáng)烈反彈和學(xué)界的不同意見(jiàn)。
剛剛頒布的司法解釋?zhuān)窃?015年的《關(guān)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行政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版本上擴(kuò)展形成的,而2015年司法解釋是對(duì)行政訴訟法的第一次擴(kuò)張,源于在中國(guó)法中植入了“行政協(xié)議”概念。
行政訴訟法,主要是針對(duì)“民告官”的程序規(guī)則,該法的第2條作出定義,明確了行政訴訟針對(duì)的是行政行為。行政行為是一個(gè)抽象概念,具體包括行政許可、行政審批、行政處罰、行政強(qiáng)制等多種行為。這些行為,有些有上位的實(shí)體法,比如行政許可法,有些列入了立法規(guī)劃,比如行政處罰法。
2014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在“受案范圍”一章中,第12條列舉了相對(duì)人(即行政法上所說(shu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訴訟理由中,與后來(lái)的“行政協(xié)議”相近的表述為,“認(rèn)為行政機(jī)關(guān)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jīng)營(yíng)協(xié)議、土地房屋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等協(xié)議的”。這里的邏輯,是說(shuō)外觀表現(xiàn)是“協(xié)議”(第12條),但應(yīng)當(dāng)內(nèi)在是行政行為(第2條),屬于行政庭的受理范圍。
但是,2015年的司法解釋將前述涉及到的“協(xié)議”直接界定為“行政協(xié)議”,創(chuàng)造了“行政協(xié)議”的概念,當(dāng)時(shí)即在法學(xué)界產(chǎn)生了諸多爭(zhēng)議。上位法方面,除了行政訴訟法之外,“行政協(xié)議”沒(méi)有在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等實(shí)體法中出現(xiàn)過(guò)。原來(lái)的行政訴訟法第12條的表述,其實(shí)是解釋政府特許經(jīng)營(yíng)協(xié)議和土地房屋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是行政行為的,但通過(guò)“等協(xié)議”的表述,創(chuàng)造了“行政協(xié)議”概念,并將其列為行政行為的一種。2015年司法解釋?zhuān)瑒t補(bǔ)充了一個(gè)“其他行政協(xié)議”。
剛剛頒布的司法解釋?zhuān)?015年確立的“行政協(xié)議”概念,形成了更大幅度的擴(kuò)張,進(jìn)一步擴(kuò)充了管轄范圍,這不僅體現(xiàn)在該司法解釋的直接稱(chēng)之為《關(guān)于審理行政協(xié)議案件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更體現(xiàn)在將“行政協(xié)議”的定義改為,“行政機(jī)關(guān)為了實(shí)現(xiàn)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務(wù)目標(biāo),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xié)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quán)利義務(wù)內(nèi)容的協(xié)議“。
同時(shí),司法解釋還將另外三種協(xié)議也納入“行政協(xié)議”管轄權(quán):礦業(yè)權(quán)等國(guó)有自然資源使用權(quán)出讓協(xié)議;政府投資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賃、買(mǎi)賣(mài)等協(xié)議;符合本規(guī)定第一條規(guī)定的政府與社會(huì)資本合作協(xié)議”。
這意味著,“礦產(chǎn)等自然資源開(kāi)發(fā)”“保障房”和“PPP”這三個(gè)巨大的市場(chǎng)將被納入法院行政庭的管轄權(quán),這種改變勢(shì)必沖擊這三個(gè)專(zhuān)業(yè)市場(chǎng)的預(yù)期,并改變相關(guān)市場(chǎng)行為。
首當(dāng)其沖受到司法解釋影響的是PPP市場(chǎng)。
2014年《預(yù)算法》修改之后,隨著公共服務(wù)社會(huì)化、公共產(chǎn)品市場(chǎng)開(kāi)放,PPP成為一個(gè)重要的市場(chǎng)構(gòu)成。盡管相關(guān)部門(mén)對(duì)于PPP的名稱(chēng)到具體規(guī)則多有爭(zhēng)執(zhí),具體操作模式也隨政策文件的出臺(tái)不斷變化,但可以肯定,PPP是一個(gè)必然且正確的改革走向。
在現(xiàn)實(shí)中,PPP已有大量實(shí)踐。截至2019年上半年, PPP項(xiàng)目入庫(kù)數(shù)量共計(jì)9036個(gè),入庫(kù)項(xiàng)目總金額達(dá)到13.64萬(wàn)億元,其中2019年第二季度凈增項(xiàng)目就已經(jīng)達(dá)到193個(gè),投資額接近2200億元。面對(duì)這樣一個(gè)巨量規(guī)模的市場(chǎng),業(yè)界對(duì)于對(duì)于制定專(zhuān)門(mén)的PPP法翹首以盼。
在關(guān)于PPP的討論之中,各方的意見(jiàn)、討論、爭(zhēng)執(zhí)已經(jīng)非常充足(參見(jiàn)財(cái)經(jīng)年刊2017:戰(zhàn)略與預(yù)測(cè),“PPP的制度困境和出路”),只是因?yàn)镻PP合同的長(zhǎng)期性、公私混合、結(jié)構(gòu)復(fù)雜而多元等特點(diǎn),在合同內(nèi)容、交易模式、模塊組成、對(duì)地方政府債務(wù)方式和控制水平上,各方爭(zhēng)執(zhí)不下。此外,這類(lèi)PPP合同究竟是民事合同還是行政協(xié)議,其司法管轄權(quán)如何界定難以達(dá)成一致。再加上政策不斷變化,PPP立法遲遲沒(méi)有進(jìn)展。
PPP涉及到眾多法律部門(mén),包括民、商、經(jīng)濟(jì)、行政乃至憲法等,盡管大多數(shù)法律人都認(rèn)為可以采用民事訴訟機(jī)制解決爭(zhēng)議問(wèn)題,實(shí)踐中很多項(xiàng)目的合同爭(zhēng)議也已訴諸仲裁。但新的司法解釋明確,PPP應(yīng)當(dāng)歸屬于行政協(xié)議,將納入行政司法管轄。
按照行政法學(xué)界采用的“大行政法”模式,將“與政府有關(guān)的行為”都?xì)w屬于“行政行為”,行政協(xié)議即是包含了“行政行為”的合同。但這樣的界定,改變了原有的法律定性。
再來(lái)看“礦業(yè)權(quán)等國(guó)有自然資源使用權(quán)出讓協(xié)議”是否應(yīng)屬于“行政協(xié)議”。
按照中國(guó)法律,自然資源歸屬于國(guó)家所有,屬于國(guó)有資產(chǎn),也稱(chēng)之為資源性國(guó)有資產(chǎn)。國(guó)有資產(chǎn)法律制度的首要原則是“國(guó)家所有(有時(shí)表述為全民所有),分級(jí)管理”,行政機(jī)關(guān)行使公共管理職能,代表國(guó)家管理國(guó)有資產(chǎn)。涉及到國(guó)有資產(chǎn)的交易等行為,在學(xué)理上仍通常認(rèn)為屬于經(jīng)濟(jì)法范疇。比如,國(guó)有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性國(guó)有資產(chǎn)),涉及到一般交易的,通常認(rèn)為屬于民事合同,再比如大部分政府采購(gòu)(行政性國(guó)有資產(chǎn))行為也屬于民事合同。
同樣的道理,在憲法規(guī)定的“國(guó)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前提之下,國(guó)有自然資源實(shí)施使用權(quán)出讓制度,這是借助市場(chǎng)的力量來(lái)物盡其用,即交由市場(chǎng)主體來(lái)開(kāi)采和經(jīng)營(yíng),以實(shí)現(xiàn)國(guó)有自然資源所有權(quán)和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兩權(quán)分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利用效率。
新的司法解釋忽視了《礦產(chǎn)資源法》中相關(guān)規(guī)定,“礦產(chǎn)資源屬于國(guó)家所有,由國(guó)務(wù)院行使國(guó)家對(duì)礦產(chǎn)資源的所有權(quán)”、以及“國(guó)家實(shí)行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有償取得的制度”中第5條的“所有”、“轉(zhuǎn)讓”的定性,僅僅強(qiáng)調(diào)出讓的一方為政府,就將這種出讓行為定性為“行政行為”,同時(shí)將出受讓雙方的合同劃歸為“行政協(xié)議”。
與其他國(guó)有資產(chǎn)相比較,對(duì)于國(guó)有自然資源的這種認(rèn)定顯然值得商榷。如果自然資源出讓是行政協(xié)議,土地使用權(quán)出讓合同、國(guó)有企業(yè)出資合同或者章程、政府采購(gòu)合同為什么不認(rèn)定為行政協(xié)議呢?
事實(shí)上,在此次司法解釋之前,邊界相對(duì)清晰:市場(chǎng)主體獲取“采礦權(quán)”證或“探礦權(quán)”證屬于行政許可行為,而同時(shí)簽訂的出讓合同,司法實(shí)踐大都是采用民事合同來(lái)對(duì)待的。這在最高法院2017年頒布的《關(guān)于審理礦業(yè)權(quán)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中也得到確認(rèn)。
那么,將原本認(rèn)定為民事合同的PPP、礦業(yè)權(quán)出讓等領(lǐng)域的合同性質(zhì)認(rèn)定為行政協(xié)議后,其管轄權(quán)的變化意味著什么?
首先,是行政機(jī)關(guān)的“違約理由“發(fā)生了變化。按照《合同法》等法律規(guī)定,民事合同一旦設(shè)立,只要不存在無(wú)效、可撤銷(xiāo)的情形,就必須依照約定履行。不能單方變更或解除,否則守約方有權(quán)要求充分賠償。
但是司法解釋第16條則規(guī)定,“在履行行政協(xié)議過(guò)程中,可能出現(xiàn)嚴(yán)重?fù)p害國(guó)家利益、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變更、解除協(xié)議的行政行為后,原告請(qǐng)求撤銷(xiāo)該行為,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認(rèn)為該行為合法的,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qǐng)求”,這就將履行過(guò)程中“可能出現(xiàn)嚴(yán)重?fù)p害國(guó)家利益、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情形”列為了不依約履行合同的正當(dāng)理由。
但是,行政機(jī)關(guān)在理論假定上就是代表國(guó)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在簽訂合同的時(shí)候,關(guān)于是否損害公共利益就已經(jīng)判斷過(guò)一次了,否則這個(gè)合同就不應(yīng)當(dāng)簽訂。司法解釋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履行中的公共利益來(lái)和簽訂時(shí)候的公共利益對(duì)抗。后果是,行政機(jī)關(guān)簽訂了合同后,可以隨時(shí)“翻臉”,作出一個(gè)新的有關(guān)公共利益理由,從而合法變更或者解除合同,這其實(shí)助長(zhǎng)了行政機(jī)關(guān)不履約的亂象。甚至可以說(shuō),是通過(guò)司法解釋賦予了行政機(jī)關(guān)單方變更和解除合同的權(quán)利。
其次,是違約賠償標(biāo)準(zhǔn)發(fā)生了變化。司法解釋第16條在規(guī)定了行政協(xié)議在履行中可以變更、解除之外,還規(guī)定了“給原告造成損失的,判決被告予以補(bǔ)償”。對(duì)比一下,第15條2款,“因被告的原因?qū)е滦姓f(xié)議被確認(rèn)無(wú)效或者被撤銷(xiāo),可以同時(shí)判決責(zé)令被告采取補(bǔ)救措施;給原告造成損失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判決被告予以賠償”,顯然15條的情節(jié)更嚴(yán)重,采用了“賠償“的表述。對(duì)照一下,“補(bǔ)償”一定是小于“賠償”的。
而上述兩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都是小于《合同法》所保護(hù)的“期待利益”的。《合同法》規(guī)定,“當(dāng)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wù)或者履行合同義務(wù)不符合約定,給對(duì)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yīng)當(dāng)相當(dāng)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guò)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shí)預(yù)見(jiàn)到或者應(yīng)當(dāng)預(yù)見(jiàn)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
第三,可以預(yù)測(cè)一下行政協(xié)議訴訟的實(shí)際效果。根據(jù)人民網(wǎng)2014年援引的時(shí)任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長(zhǎng)王振宇的介紹,中國(guó)行政訴訟的特點(diǎn)是原告的勝訴率即被告的敗訴率低。10年前被告敗訴率占30%左右,近年來(lái)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另一則公開(kāi)數(shù)據(jù)是,2016年,全國(guó)各級(jí)法院共受理一審、二審和再審行政案件331549件,同比上升10.6%,新收加舊存案件共計(jì)386886件。2015年審結(jié)的一審行政案件中,行政機(jī)關(guān)的敗訴率同比小幅上升,行政機(jī)關(guān)在行政訴訟一審中敗訴的案件共計(jì)32895件,敗訴率為14.62%,同比上升0.84個(gè)百分點(diǎn)。
綜合其他公開(kāi)信息可知,盡管行政訴訟的勝訴率存在省際差異,但在大多數(shù)省份呈下降趨勢(shì)。如果將時(shí)間線拉得更長(zhǎng),這種趨勢(shì)更為明顯。
在最高法院召開(kāi)的新聞發(fā)布會(huì)上,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表示,這部司法解釋的發(fā)布,將對(duì)切實(shí)保障人民群眾在行政協(xié)議中的合法權(quán)益、推進(jìn)法治政府誠(chéng)信政府建設(shè)、優(yōu)化法治化營(yíng)商環(huán)境、提高政府行政治理能力、推進(jìn)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產(chǎn)生積極的、深遠(yuǎn)的影響。
但是對(duì)比現(xiàn)實(shí)中的行政訴訟現(xiàn)狀,很難期待這份司法解釋能夠?qū)崿F(xiàn)初衷。
司法解釋擴(kuò)張了行政協(xié)議,對(duì)PPP這個(gè)還沒(méi)有上位法的領(lǐng)域,影響是巨大的,因?yàn)闆](méi)有實(shí)體規(guī)則的上位法,司法解釋第2條就成了唯一的PPP規(guī)則。同時(shí),而后制定的規(guī)則,都要受制于這種“在先”的規(guī)則。
PPP合同具有長(zhǎng)期性特點(diǎn),短則數(shù)年,長(zhǎng)到幾十年,在如此長(zhǎng)的時(shí)間跨度內(nèi),“國(guó)家利益、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內(nèi)涵外延都會(huì)發(fā)生變化。原本不允許的現(xiàn)在允許了,原本允許的現(xiàn)在不允許了,這種就是改革的常態(tài)。
如果將政府行為都?xì)w為行政行為的話,適用現(xiàn)行司法解釋?zhuān)谌绱碎L(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行政機(jī)關(guān)隨著規(guī)則制度的變化,通過(guò)簡(jiǎn)單的行政行為就可以變更或者解除合同,而賠償降低到了“補(bǔ)償”,這如何能切實(shí)保護(hù)市場(chǎng)主體的預(yù)期?
行政機(jī)關(guān)在簽訂PPP合同的時(shí)候,按照合同法,只要有效,單方就不能變更和解除,這才能保護(hù)私人投資者的預(yù)期。可司法解釋允許行政機(jī)關(guān)數(shù)十年的履行中單方變更或者解除,而此時(shí)補(bǔ)償?shù)臉?biāo)準(zhǔn)更傾向于實(shí)際發(fā)生的損失,而不是按照合同可以得到的完整利益賠償,就會(huì)對(duì)PPP市場(chǎng)主體形成負(fù)面激勵(lì)。
合理預(yù)測(cè),在這一規(guī)則下,私人投資進(jìn)入公共服務(wù)、公共產(chǎn)品市場(chǎng)的積極性可能萎縮甚至消失,或者市場(chǎng)預(yù)期嚴(yán)重降低。另一個(gè)可能性是,這將加劇財(cái)政部一直反對(duì)的PPP亂象之一——私企不熱國(guó)企熱,加劇PPP從政府與社會(huì)資本合作的初心,變形為政府與國(guó)有資本合作的怪象。PPP的特點(diǎn)是一次投入,長(zhǎng)期回收成本和收益,規(guī)則對(duì)于這個(gè)市場(chǎng)的影響之大,可能是這份司法解釋所沒(méi)有通盤(pán)考慮的。
我認(rèn)為,不應(yīng)該在沒(méi)有實(shí)體法的前提下去用司法解釋為PPP定性,因?yàn)槿狈貦?quán)機(jī)制,也容易被規(guī)避。作為復(fù)雜的PPP合同,許多問(wèn)題還沒(méi)有在實(shí)踐中完全暴露出來(lái),用一份僅有29個(gè)條文的司法解釋能解決要調(diào)整的問(wèn)題嗎?
隨便舉個(gè)例子: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時(shí)候,通常是“一切都好說(shuō)”,那么如果企業(yè)和地方政府在合同之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條款,“本協(xié)議不涉及行政行為,屬于XX政府基于對(duì)XX的所有權(quán)管理而簽訂的民事合同”,這并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符合合同法,行政庭根據(jù)何種規(guī)則去認(rèn)定這不是一個(gè)民事合同呢?合同設(shè)計(jì)和表述在市場(chǎng)上是“充滿(mǎn)活力”和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的,行政庭在缺乏裁判實(shí)踐的情形下,低估了合同領(lǐng)域的復(fù)雜性。
盡管司法解釋不一定完全是“限縮性”解釋?zhuān)且鶕?jù)立法目的來(lái)構(gòu)造規(guī)則,但在沒(méi)有實(shí)體法的前提下,立法目的如何解釋?zhuān)?/span>
自2004年的《行政許可法》頒布之后的各屆政府,尤其是本屆政府,一直致力于嚴(yán)格的控權(quán)思路。剛剛頒布的《優(yōu)化營(yíng)商環(huán)境條例》,實(shí)際上是政府與市場(chǎng)關(guān)系的總綱領(lǐng),它以法規(guī)的形式重申了一直以來(lái)強(qiáng)調(diào)的“放管服”。國(guó)務(wù)院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要限縮行政權(quán)力,嚴(yán)控行政行為,各級(jí)政府應(yīng)當(dāng)守約。而司法解釋賦予了行政機(jī)關(guān)履約中單方變更和解除權(quán),和這樣的改革思路是相符的嗎?
雖然司法解釋制定主體是司法機(jī)關(guān),但涉及到行政行為,符合《優(yōu)化營(yíng)商環(huán)境條例》第64條“沒(méi)有法律、法規(guī)或者國(guó)務(wù)院決定和命令依據(jù)的,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不得減損市場(chǎng)主體合法權(quán)益或者增加其義務(wù)“的規(guī)定嗎?
將PPP定性為行政協(xié)議,實(shí)際上借鑒的是法國(guó)模式。但是為什么不去考慮除了法國(guó)之外的其他模式呢?英美法律中都是采用民事訴訟機(jī)制解決的,即便是同為大陸法系的德國(guó),PPP也大多數(shù)采用民事訴訟機(jī)制。
不光如此,中國(guó)已經(jīng)簽署了《解決國(guó)家與他國(guó)國(guó)民間投資爭(zhēng)端公約》(ICSID),最近又通過(guò)了《外商投資法》,給國(guó)際投資者以準(zhǔn)入前的國(guó)民待遇。另外頒布的《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擴(kuò)大對(duì)外開(kāi)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確提出進(jìn)一步擴(kuò)大改革開(kāi)放,更具體規(guī)定了“支持外資依法依規(guī)以特許經(jīng)營(yíng)方式參與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環(huán)保、市政公用工程等。相關(guān)支持政策同等適用于外資特許經(jīng)營(yíng)項(xiàng)目建設(shè)運(yùn)營(yíng)”。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guó)將實(shí)施更強(qiáng)的國(guó)際化開(kāi)放政策,外資進(jìn)入PPP等領(lǐng)域是必然的趨勢(shì)。但是按照司法解釋第26條,“行政協(xié)議約定仲裁條款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確認(rèn)該條款無(wú)效,但法律、行政法規(guī)或者我國(guó)締結(jié)、參加的國(guó)際條約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這意味著,外資進(jìn)入PPP,依據(jù)ICSID,外國(guó)投資者可以在境外針對(duì)中國(guó)政府提起國(guó)際仲裁——這類(lèi)案件已經(jīng)發(fā)生;而國(guó)內(nèi)投資者則要大概率被劃為行政協(xié)議訴訟。這樣一來(lái),會(huì)造成新的內(nèi)外不平等。
這種不平等不但可能在中國(guó)國(guó)內(nèi)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還可能會(huì)對(duì)中國(guó)企業(yè)“走出去”形成障礙。試想,如果中國(guó)企業(yè)進(jìn)入一些國(guó)家的公共產(chǎn)品市場(chǎng),而這些國(guó)家都來(lái)模仿行政協(xié)議的做法,后果會(huì)如何?
司法解釋引發(fā)的問(wèn)題和對(duì)市場(chǎng)的影響,遠(yuǎn)不止本文所談到的。問(wèn)題的根源在于:既然是牽涉到多個(gè)法律部門(mén)交叉,又事關(guān)多個(g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還涉及多個(gè)政府部門(mén),并觸及公私融合的問(wèn)題,司法解釋在起草過(guò)程之中,也一直存在著種種的異議和爭(zhēng)論,這正體現(xiàn)在起草者自己所稱(chēng)的,聽(tīng)取了很多意見(jiàn),花費(fèi)了時(shí)間,修改了多稿。這里不禁要問(wèn),既然意見(jiàn)尚未統(tǒng)一,為什么還要急于出臺(tái)司法解釋而“單兵突進(jì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