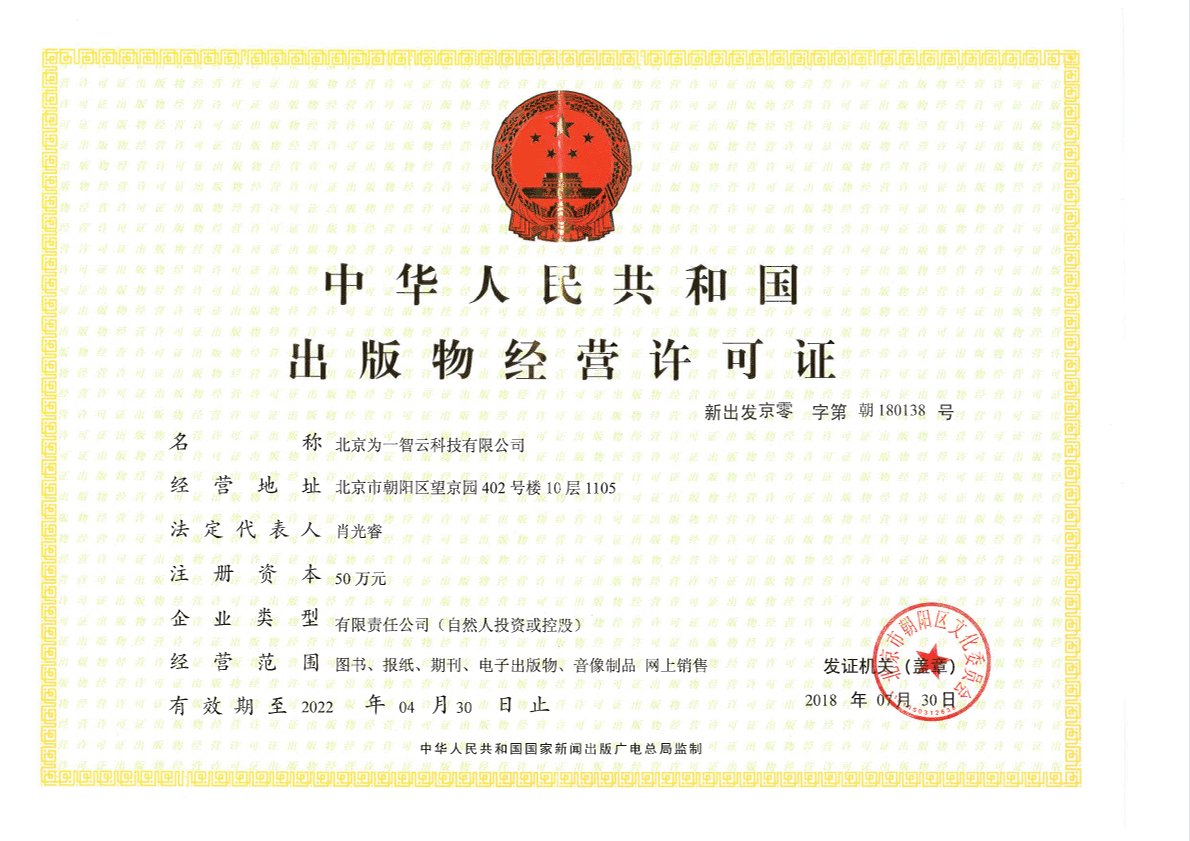10月底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全文尚待公布,但書記對《建議(審議稿)》的說明已經引發各方強烈關注,各行業都對涉及自身的“只言片語”進行了引申解讀,有些甚至還不吝筆墨撰文細究。
在未來城市發展格局上,全會提出:
“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要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這個決策方向更加注重區域發展的“均衡”,使得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未來大城市繼續集聚發展的效率優先之路將被放棄。
孚園對這個“放棄”論有不同看法。
城市的底層驅動力固然來自產業集聚所形成的“專業化”,也就是城市為了將產品和服務銷售到城市以外而將產業人口集聚在一起:企業因為潛在勞動人口的集聚而降低了自己的創業成本,勞動人口反過來又因為企業的擇址而依企業而居。
雙向循環互相加強,讓城市能夠形成自己的專業化優勢,從而塑造自己獨特的競爭力。
但該如何衡量集聚的程度,并以此確定一個城市的產業是否集聚充分?
有實證研究表明,同一棟寫字樓內三層以外的用戶基本不會有交集,而城市兩端的企業反倒可能會共享相同的供應商。對此經濟學還沒有明確的答案。它只是說如果城市的人口足夠龐大、人們住得更為緊密,我們就越能相互碰撞、從多樣化的彼此身上獲得各類靈感——但我們并不知道它實際是怎么發生的。
那么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城市的集聚規模是否有一個合適的體量上限,超過這個體量之后,即便城市規模更大,我們彼此也無法產生更多的“交互”火花?
孚園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通勤時間是一個有效指標,它衡量勞動力參與到產業之中的時間成本——我們或許能從城市集聚的產業中分享和學習更多,但如果這個時間已經漫長到影響日常作息與精力再恢復,那自然是不可持續的。這正是“集聚”的副作用,人們為爭奪這個有限的集聚空間而花費了大量到達這里的時間:
盡管我們一方面向天空要空間,另一方面建設軌道交通而節省時間,但都難以將集聚的副作用平抑到日常生活可接受的水平。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像倫敦、紐約和東京這樣的大都市在這些年不斷吸納人口,但核心區卻維持了原有的基本面貌(圖1)。
圖1:東京核心23區常住人口規模在1965年達到頂峰約990萬人后不斷溢出,隨后三十年減少了近90萬(而同期郊區人口增加了2000多萬人),直到2010年中心城區的“復興”,人口比1965年峰值超出約5萬。
如果比較我國上海、北京和紐約、東京都市區的人口分布,發現相較后兩者,上海和北京的中心城區(0~10km)常住(夜間)人口密度要高得多(圖2),工作日白天更甚(圖3)。
圖2:我國上海和北京中心城區常住人口密度要遠高于東京和紐約,10公里區域內每平方公里人口總量分別為2.56萬人、2.07萬人、1.32萬人和1.31萬人
圖3:工作日白天大量居住在10~30km中的人口奔波到中心城區上班,導致該區域內人口密度大幅下滑。在10~20km區域,原本上海和北京人口密度最高,但最終分別下滑到每公里0.52萬人和0.64萬人,而東京和紐約分別還有1.0萬人和0.7萬人
相較東京和紐約,上海與北京這樣的國內大都市顯得更加“不均衡”:
一是行政服務和優質公共資源仍然明顯集中在內城核心區,不斷吸引市場要素向市中心集聚,人口和企業難以外遷;
二是工業化轉型還在半途,10~30公里范圍內仍有大量工業用地,商業和居住用地比例相對較低,難以在本區域內疏導城市職住功能。
當然,東京和紐約也有自己的問題。東京都市圈的人口規模過于龐大(超過3800萬),雖然東京建造了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快速通勤鐵路系統,上班族公交出行的比例也是世界首位,但城市規模過大仍然讓通勤問題難以消弭(暫且忽略軌道交通過于擁擠的體驗問題,圖4)。
相比之下,紐約都市圈的人口因為只有2030萬,雖然也存在工作崗位在曼哈頓集中、公交出行比例低(公交設施不夠發達)等問題,但總體上來說,紐約的出行時間要比東京更為合理(圖5):平均通勤時間為37.9分鐘,比東京中位數低了17%。
圖4:東京居民出行時間分布,中位數為45.9分鐘。其中通勤時間最長的是居民集中在距市中心10~40公里的區域(20~30公里區域的平均出行時間最長達54.9分鐘);40公里以外的職住平衡度更好,出行時間較短
圖5:紐約都市區出行的平均時間為37.9分鐘,雖然比美國全國平均26分鐘要高出很多,但相比東京45.9分鐘的出行中位數,仍然要通暢得多
當前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要比紐約都市區都略高,分別為2428萬和2154萬,但其通勤時間不僅遠超紐約,甚至比東京更長。前程無憂發布的《2018職場人通勤調查》顯示,上海平均通勤時間達到59.6分鐘,分別比東京和紐約高出30%和57%;北京六環內的平均通勤時間也高達56分鐘,擁堵程度不遑多讓。
中國的其他大都市未來繼續擴容,若都以北上為范本,顯然不是國家樂意看到的。對《建議(審議稿)》的說明,可以說是就過去幾年中西部省份不斷突出省會城市首位度趨勢的一種修正。后來者雖然可以吸取北上的城市規劃教訓,拉平中心城區向外的人口密度坡度,讓職住更加平衡,但依靠不斷擴張城市邊界來“集聚”出大都市、甚至靠吸納周邊中小城市的資源為代價的打法,已經再難為繼。最近書記在《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一文中就直接指出我國的城市化戰略:
“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是客觀經濟規律,但城市單體規模不能無限擴張……要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城市之間既要加強互聯互通,也要有必要的生態和安全屏障。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
從長遠看,國家已經意識到,我們的超大城市雖然集聚出了產業效率,但卻損失了“人口的再生產”。我們亟需改變方針策略,在產業集聚、日常活動空間、人口再生產以及生態安全上找到新的平衡點。
問題是,這可以做到嗎,又該怎么做?
答案首先是肯定的。
我國嚴格的土地紅線制度來自于主糧安全(這曾經一度是發展大城市的主要因素,因為大城市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積更小),但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我國已經成功實現在灘涂等鹽堿地上耕種水稻,這等于實際擴大了可開發城市總面積。同時,未來隨著能源總成本的進一步降低,城市垂直農場在商業上最終可行之后,將進一步提高耕地安全性——尤其是考慮到我國人口規模將在2030年前后見頂,耕地最大面積負荷減輕之后,我們就有更多的土地空間來開發出“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從而可以逐漸規避大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和逼仄的生活空間。
但人口在網絡型城市群的分布最終會損害產業集聚的生產效率嗎?
大可不必擔心。
一是依托信息技術的發展,本身已經逐步擴大了“居家辦公”的范圍,尤其是本次疫情后,很多企業可能會直接縮小辦公規模,將更多員工脫離工作日每天的通勤之苦。斯坦福大學教授Nicholas Bloom的一項聯合研究顯示,美國疫情前有5%的勞動人口已經長期在家辦公,疫情期間該比例飆升到42%。他預計疫情后,社會對“居家辦公”這個詞脫敏后,整個社會的比例最終將穩定在20%左右——1/5的勞動人口將“永久性”不會重返辦公室。當然,并不是說這些員工都可以遠走高飛了,比較典型的情況是,很多員工會選擇一周在家辦公1~3天,其余時間仍然到辦公室處理那些需要當面接洽的事務。
美國居家辦公的趨勢已經讓過去十年重新復興的市中心出現了再次衰退的跡象,與之相反的是大都市周邊郊區甚至農村地區的繁榮。
中國會發生美國的這種情況嗎?程度上不一定,但趨勢上一定。當前國內 “居家辦公”模式在職業倫理上仍沒有徹底擺脫污名,但未來這將成為優秀員工可爭取的福利之一,如果再考慮企業由此可節省大量辦公成本,預計這個模式在國內推廣并不困難。
進一步思考,如果員工不需要再承受每日通勤往返之苦,而只用每周2次往返,我們能承受的通勤距離會是多遠?答案是比我們想象的更遠。
事實上,同濟大學相關研究顯示,當前長三角區域內有5.7萬人選擇跨城通勤(其中蘇州-上海間占到總數的88%),他們依賴出租車-高鐵-地鐵這一無縫連接系統,在家和辦公之間來回奔波——如果在家辦公的人口比例上升到10%,上海每天的跨城通勤人數達到100萬,那應該怎么調整?
顯然是繼續加強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
大城市和鐵道部門合作,開發直通市中心核心地鐵站點的通勤線路,對跨城上班族售賣月票。
如果居家辦公員工單程可接受的通勤時長為1.5小時,算上兩邊接駁和換乘時間,搭載通勤鐵路的時間以一小時計,以200公里/小時車速,算上啟停間隔,大城市的市中心延展距離將輕松達到100公里。
這不僅能將各大城市更加頻密地聯通起來,更重要的是,也將極大地擴大核心城市的投射腹地——試想如果選擇在通勤鐵路停靠站點周邊有針對性地開發,逐步將核心城市內的部分資源騰退過去之后會如何?甚至以某個站點周邊的特殊資源為基礎,去開創某類特殊企業(或者吸引相應企業前來落址)又會如何?
如何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建立“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我們應該在信息技術重塑工作場景的大時代背景下,繼續挖掘我國軌道運行和管理技術,圍繞核心城市推廣新型的、基于郊區甚至農村的TOD項目,讓城市建設、人口就業和公共服務同步發展,真正踐行“城鄉居民平等參與城鎮化進程,共同分享城鎮化發展成果”的理念。
如此這般,孚園認為新型的TOD項目也將切實回應“十四五規劃”對新型城鎮化的實質訴求:
“以人為本!”